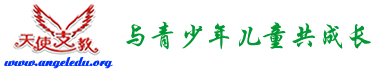支教总结-离开在山花烂漫时
2013-03-25 08:00:00 来源: 点击:
我时常会想为什么来这支教,当初的迷惑此时未解,但这些日子所感受到的生活的滋味是如此甜美,我那么喜欢。或许对别人来说,支教是艰苦的,对我而言,支教是奢侈的,如果可以,我想一直待下去。回到广州,我觉得自己像棵被连根拨起的小草,移植到统一照料的植物园,虽然不会枯萎死去,却有所残缺。
 每次我都是背着家人过来的,火车上,我给从小疼爱我的哥哥发短信:“大,我去湖南了,谢谢一直以来你对我的照顾、开导和体谅,但我还是看不清人的一生究竟为何,或许不会有唯一的答案,却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让我安心立命的理由。你好好保重。”我对人生充满迷惑,来支教,不是为了帮孩子,而是帮自己。 怀着即将离开的心情看眼前的场景,似乎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公路盘山、云雾缭绕、山峦秀丽。 ** 我喜欢和孩子们玩在一起,每每想到自己终究会离开,不属于这里时,我便多么希望能够像卢老师那样把自己完全交给孩子,让孩子们尽情地使用我。虽然培训时卢老师说过来支教不需要想法,但很少有人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支教的。尽管我自称是卢老师的忠诚粉丝,我也忍不住会去构想如何培养学生、如何建立师生关系,应该做个怎样的老师。 特别是这个学期回到这里,看到新的志愿者身上或多或少有些自己去年的影子时,我便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错。一开始我以为孩子们会很喜欢支教老师的。一个敏感的女孩说:“我们不喜欢新老师。不过詹老师我喜欢你,上学期你教我们唱《我们都是好孩子》时我就喜欢你了。”教那首歌时我差不多上了他们一个月的课了,也就是一开始一个月的时间里孩子们并没有真正接受我,尽管我几乎每天给他们上艺术课程。孩子们喜欢能够陪他们、让他们感到安全的老师。就像当地的施老师,孩子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会跟孩子们玩,虽然他普通话不太标准、课堂没多少新花样,但他是真正爱孩子的老师。施老师不懂怎么上艺术课,但每次美术课他都会拿着简笔画在黑板画几个简单的图案让孩子临摹,音乐课会用自己的手机放孩子们会唱的歌让大家一起唱。别说是当地老师了,就算是大学学历以上的志愿者也很少人会有这个心思去上这些课。 上学期教他们唱《我们都是好孩子》时,我把那两个星期所有的美术课都改成音乐课,只教一首歌。好长一段时间,学校的广播里单曲循环地播放这首歌,而我跟孩子们就在旗杆前边唱边做着手语动作。有时一节课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孩子们只是觉得有点累,却没有感到厌烦。早上上课前,孩子们会要求我播放这首歌,然后我们在旗杆下做手语动作。每次唱到“你”时,他们便把手指向我或其他的老师,这让他们感到很兴奋。我想孩子们之所以不会厌烦,反而那么兴奋,是因为他们需要一种稳定的力量。因此我便把艺术课程的安排调整了一下,一个星期都上音乐课,一个星期都上美术课。而孩子们很愿意合作。 我更多的关心他们心灵的成长,因此更注重艺术教育。但主课还是让我感到头疼。二年级的孩子很调皮,宏文上课经常跑到同学那去打扰他们,龙江经常自言自语说一堆我听不懂的苗话,文杰一上课就在那摆弄着文具盒或削着铅笔或玩弄其它的东西,但就是不听课,灵鑫经常吐痰又爱说其他同学父母的名字,梦红时常一副心不在焉而且愁眉苦脸的样子,晓玲一下子就把脚放到凳子上、身子趴在桌子上,珍峰时不时得意忘形地在座位上扭着身子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晶晶则不时说同学坏话,不时玩弄同学,不时离开座位……虽然每星期只有6节数学课,但班上孩子的数学期末考试平均分还是在乡里遥遥领先,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按孩子喜欢的方式上数学课,比如不让他们抄写数学题目,见他们不在状态时一起玩数学游戏。而且我发现当孩子们做作业时老师在一旁的话他们会更愿意做。二年级的孩子喜欢做数学题,但要及时批改讲解,孩子们看到成果后会有动力。 ** 一开始我确实有不少想法,比如每天早上给他们讲故事,比如自编故事和曲子……但其实这些想法不重要也不需要,因为我还没理解孩子们的需要,当我理解时,我便知道怎么做了。其实大多时候我并没有看到孩子们的需要,只是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这样好、那样好。 如果我能更多地根据孩子们的需要做出反应,我想我会在教育这条路走得更深远些。 ** 关于孩子们 这里的孩子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缺乏什么、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一次语文课上我让他们说说自己的烦恼,他们所说的烦恼都是同学之间相处的一些矛盾,比如谁上课老抓弄谁了,谁老是说坏话了。我尝试着引导他们:你们不觉得一年到晚见不到爸爸妈妈很难过吗?嘴快的晓玲拖着长音说:不觉得啊——其他孩子不好意思地笑着。他们当然想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不意味着会因得不到而难过。记得寒假看央视新闻频道的共同关注,播了贵州一个叫污讲小学的孩子的采访。记者问孩子们最想要的是什么,由此强调很多孩子都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其实孩子们心里有这个愿望,但只有当被赤裸裸地凸显放大出来时,孩子们才会感到心里不平衡、难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这样的凸显并没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实现他们的愿望,这么做更多是为了城里人空虚的心灵,挖别人的伤疤来刺激自己的同情心。 班上有个孩子,每天得自己一个人走1个多小时的路来上学,没有任何人陪同。一般孩子上学都会结伴而行,因此长途跋涉对他们来说是游戏的一部分,天还没亮他们便奔向学校,在小小的山坡上“跳山崖”、一路“开车车”狂跑,半个多小时便到了学校;放学回家,他们便扎入大自然中:踩泥巴、摘野果、捡树枝、滑草、打闹……少说也要两个小时才到家。但那孩子的寨上只有他自己是读一二年级的,他每天踩着泥泞的车路,两旁难见一草一树一人,沉默的大山在脚下躺着,离头顶那么近的蓝天也默不作声。那孩子更是一句话也没说,他才8岁。我问他,你不觉得每天都要自己一个人走那么长的路很辛苦吗?他腼腆笑着:不辛苦,因为家在前面。 这里的孩子并不缺乏什么,但他们需要一个好老师,一个能陪伴他们的人,能把自己交给学生的人。像当地的施老师,他不顾形象不顾面子地陪孩子们玩在一起,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把自己也当成孩子。整理支教期间的日记时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龙老师了,因为他并不爱立口的孩子。临走时龙老师问我,孩子们那么喜欢你,他们有没有哭啊?肯定没有啦~他们会舍不得,但不会因此难受。这才是健康快乐的孩子,会怀念,但不会沉缅其中。 立口的孩子像一块块没浸染的布,呈现的全是孩子的本真。12月初卢老师来听课,我的课堂闹成一团,孩子们不会因为有人来听课就表现得很乖巧。而吕洞、夯吉的孩子都在听课那天变得十分听话、乖顺。卢老师住在俄力学生的家里,我们放学一起回家。一路上,孩子们缠着卢老师“老卢、老卢”地喊,教他学苗话,跟卢老师学德语,问卢老师一堆问题。这学期石校长过来,一个孩子见他便好奇问:“你这只眼睛怎么这样?”石校长说:“你这样问是很没礼貌的。”反正我不喜欢。 孩子需要的公平 8、9岁的孩子问大人要糖时并不真的想吃,你不给,他不会觉得难受;你若给他,他便觉得这就是你能给的,而他真正的需要开始埋藏。他们开始不那么偏向喜欢陪他们一起玩、给他们糖的大人,而倾向于喜欢有某些品质的大人,特别是能让他们感到稳定的人。这个年纪的孩子也常常嚷着要公平,他们也在跟外界学习什么是公平,怎样处理公平,但孩子们自有一套情感的机制去感受。他们强调公平,但物质上的公平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更能感受到的是老师在处理事情时对他所传达的情感。 有时我让孩子帮我做事,有的孩子会说没有奖励我不做。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后来我发现他们要的奖励、谈的条件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比如物质上的糖等。不妨试着以孩子的姿态跟他们来场公平的交易,这不仅有趣,还会发现孩子们的思维的一片天地。一个孩子说,我们越长大变得越懒了,以前爸爸叫我帮忙我很愿意去,现在我不想去了。我想是因为年纪小的孩子参与工作是件很快乐的事,而稍大了,他们开始对抽象些的东西敏感。 与孩子们相处 我喜欢跟孩子玩,一开始我会想着一些游戏大家一起玩,其实没必要,孩子们的游戏已经很丰富了,我只需参与进来就可以了,很多东西我都得请教他们,他们也乐意教我,比如开火车、跷跷板、开车路、“保卫家乡”、跳皮筋等等。中午吃面条我也喜欢和他们一起,有次学期的石校长来看孩子们的营养午餐,我捧着个碗跟孩子们一道吃,问他吃不?他说要等孩子们吃完剩下了再吃。言外这意是怕孩子们不够吃。其实孩子们心里是宁愿少吃一两口面条也希望老师陪他们一起吃的。我喜欢抢他们碗里的面条,因为加了方便面的料,吃起来更美味。有时他们也分我调味料。 到了周末我就往学生家里跑,顺便去夯沙买东西。俄力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二年级的孩子大都是那里的。他们放学回到家会先做作业,也有的到了晚上才做。没作业时就跑出去玩,有时到同学家里,有时去树林玩。树林里有好些高大的古木,落叶铺在地上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空气里尽是树木与落叶的味道。我们经常在这里爬树、荡树枝,或几个人面对着站在边缘的一根弯曲的树枝上,像摇橹那样两边摇动。卢老师来的那次,我跟孩子们说,把卢老师带这来玩,他一定喜欢的。宏文听了,霸道地说:“卢老师是我的,我不准你命令他。” 处理孩子之间的矛盾是不少志愿者头疼的事,但在立口却是件很有趣的事,我也是跟孩子们学的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你能想象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边哭鼻子边说没关系吗?立口的孩子就这样。当同学间出现不愉快时,其他孩子会充当和事佬,一个孩子把事情告诉老师,一个孩子让不对的同学向对方道歉,又让受委屈的同学说“没关系”。一般只要欺负人的同学说了“对不起”,受欺负的孩子都会说“没关系”。也有孩子还哭的,这时做老师的派上用场了。不过我不哄哭的孩子,而是让欺负人的孩子把哭的孩子逗笑。有时哭的孩子一听这话就乐了,有时围观的孩子做着各种鬼脸,欺负人的孩子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着。 其实离开并没有太多不舍和怀念,我对自己说,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便没什么遗憾了。我想我终究还是会回去,不一定是湘西,却是我一心向往的乡村和孩子。 如果你有兴趣报名参与乡村支教,请访问:天使支教2013年秋季乡村支教志愿者招募 |
- 上一篇:2013春季乡村支教培训心得-张钺
- 下一篇:2013春季乡村支教培训心得-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