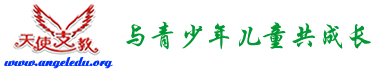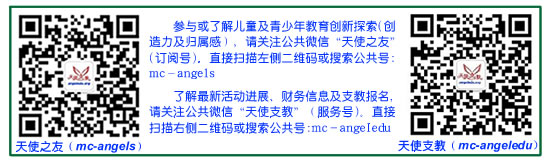|
小编按:这篇文章虽然有点长,但值得耐心的细读。
中国现今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对学生创造力的摧毁。中国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也正是创造性人才的缺乏,独立性格的缺乏,社会生活中人们趋同、从众的趋势极其严重。当然这是多种因素与教育合力的结果,教育对此当然负有责任,但是要教育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客观、不合理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因素都渗透到教育中,政府、家长、学生的需求都作用于学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社会竭力去摧毁其成员的创造力的代理部门。尽管如此,一方面教育对之有负有独立的责任,另一方面从教育领域可以集中透视出我们对创造力的摧毁,因为它是培养人才的部门。
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的未被宗教征服的民族。因此比较其他民族,我们的性格中有最为深厚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少形而上的关照,少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最理性。理性不是与科学接近吗?但哲学家陈嘉映告诉我们那是“罕见的、奇特的结合”。在更大的概率上,更惯常的意义上,理性更容易与技术结合。因为技术可以给人类直接的、切实的帮助。而最初的科学思考与神话和宗教一样,不当吃,不当喝。它们是超越现实生活、远离实用功能的。直观地看,投入到此类活动中,实在不理性。而神话与宗教的思维特征也确实是非理性。
如果区分解释性的神话与唯美的神话,理论就起源于解释性的神话。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自己种族的起源、人的生活的规范。这些都是早期理论继承下来的话题。一般说来,理性态度是反神话的。
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兴趣,它不是从轴心时代兴起的理性的态度发源的,毋宁说它发源于神话。然而,希腊人把理性的态度引进了理论探究,造就了一种新的理论兴趣,尝试了以希腊—西方为代表的哲学—科学传统:哲学—科学营建理性的理论,取代了神话式的理论。但我愿不惮其烦地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奇特的结合,是个例外。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但远不是最富理论兴趣的民族……这两方面很可能相互关联。我们的神话系统没有得到完好的保存,我们不信宗教,我们设计了完善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尽管思想、文学、艺术、历久繁荣,技术创新一浪一浪,我们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哲学—科学传统,这些事情看来是相互关联的。(陈嘉映,2005,107)
两种态度与神话和宗教对峙,即理性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一对照无可避免地提醒我们,理性的一个侧面就是现实主义。其另一侧面无疑是指逻辑指引下的思考。理性的这两个层面在世俗生活中每每便利、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科学最大程度地发扬了理性的一个层面——逻辑思考,与此同时,与另一层面至今保持相当的距离,它远没有技术那样现实,他造福人类常常是间接的,有着巨大时间跨度的。理性的这一层含义深藏在世俗语义中,当我们说某人太“理性”时,常常不是说他太“重逻辑”,而是说他不够超脱、浪漫、批判。汉民族最大地浸淫在理性的现实主义层面中。艾恩说:
现实主义意味着堕落,绝对的现实主义意味着绝对的堕落。(1993,182)其意指是多方面的。而笔者以为,在创造力方面尤其如此,过度的现实主义意味着我们民族创造力的堕落。
接下来谈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同创造力的关系。默里在其《文明的解析》中说:
把职责、家庭和求同奉为首要价值观的文明,受到的束缚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表现各不同。……科学方法的动力——为了给科学大厦再添一块砖而展开的无休止的辩论和激烈竞争——似乎需要一种基于西方模式之上的个人主义精神。没有个人主义也可以增加知识,但若要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个人主义的作用甚大。(默里,2003,393)
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奠基人通达圆熟地理解群体与个性的关系。孔子说:和而不同。近现代罕有学人如潘光旦一般得此真谛:
第一,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思想,总不能不承认两个对象的存在,一是个人,二是社会。第二,它得承认,这两个对象,要是发展得正当,是不冲突的,并不是不两立的。西洋社会思想界所有的群己权界的争论,以至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森严壁垒,都不妨说是庸人自扰的表现。(潘光旦,1939)
其实二者的尖锐对立最多地发生在两个场合,一个是历史的转折期,一个是平庸学者的著作中。后者受到转折期冲突的刺激,以为二者的对立贯穿人类历史。客观评判古代社会中二者冲突的程度难乎其难,若有夸张,其实意在沛公,即呼唤当代个性解放。个体拥有的自由空间,在古代与今时当然是不等的。笔者赞同默里所说,个体的自由对创造力至关重要。但在古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较少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制约不大。因为社会发展对科学和创造力的倚重,是近现代的事情。个体自由的扩大,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使然,如涂尔干所说有机纽带取代了机械纽带,乃至城市化,就业方式,核心家庭,等诸多变化合力造就的。在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个人主义崛起的历史转变中,中国大大地滞后于世界主流文明。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抑制了城市化,持续至今的户籍制仍然没有给进城的农民充分的自由;独子政策导致孩子没有获得多子女在核心家庭——极大地不同于生活在大家族——中拥有的自由;当然还有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惯性。凡此种种导致中国人性格上趋同、从众、缺乏多样性,影响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政治上的大一统当然不乏积极的社会功能,但其严酷的管束难以促进文化的繁荣。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和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均繁荣于政治分裂的时代,是耐人寻味的。人类创造力的勃发是近现代的事情,在古代即便一直是分裂或分治,创新也不会一浪接一浪。现代社会的发展倚重于川流不息的创新,当代大一统政治对文化和教育的管制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最后要说到的是科举制。科举制支撑起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官员产生方式,并以此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其筛选出的人才在智商上是优秀的。其最大的弱点是,不但不可能筛选出,甚至极大地扼杀着有创造潜力的人。原因简单到不必多说,应试的程序配合严酷的竞争,驱赶考生们通过无休无止的复习,去适应和精通一种模式。科举制是中华民族在制度建设上为人类做出的为数不多的伟大贡献之一。其奥妙值得当代考试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持久地研讨。你可以选择任意的视角,但是不可以时空置换,以一个事物在今天的利弊看待它在古代社会中的得失。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科举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上层人士的定位,和社会管理者的产生。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因此古代的科举制没有扼杀创造力的大罪过,有大问题的是科举制的列车竟然装载着数理化等科目驶进了当代社会。依旧是无休无止的复习,且因科目的增多,今天的学生比古代举子复习(我们不说学习,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负担重得多的。依旧凭单一的考试来筛选,其他的方式,推荐、面试等等,因社会信任的降低不被采用,或徒具形式,于是独木桥上的拥挤达到空前。更因为教育的大众化导致今天的竞争十倍于古代,乃至现代科举制对创造性的杀伤力也十倍于古代。
至今为止,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接受了12年中小学教育的十亿人口中没有一人获得科学诺贝尔奖。这雄辩地说明了,教育可以在何等程度上代理和协助其社会扼杀创造力。
来源: 《信睿》2012年11期
欢迎关注天使支教相关公共微信平台,参与相关话题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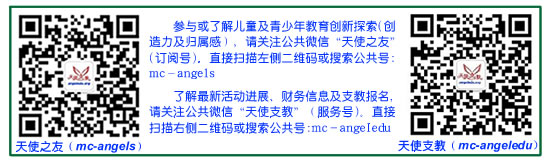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