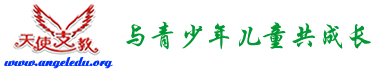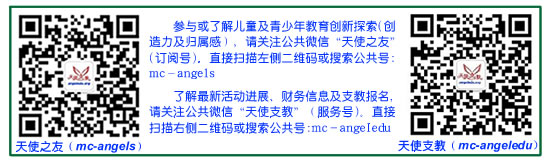几个星期前,我看了一场八个钟头的话剧,从下午到午夜,疯狂而满足,戏是赖声川的《如梦之梦》。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台大医学院刚毕业的医学生,第一天去医院上班,遇上了五个病人,死了四个,剩下一个垂死者,她也无能为力。这时,她突然感到了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的无力,那种从小建立的信念与信心开始动摇。对于医学尚无法救治的病人,作为医生的自己可以做什么呢?她在自己的医生家族里,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们告诉她不要把自己的个人感情牵扯进来,要用专业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医生只能治病,但是治不了命。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答案,她叩问:难道我们就不能做点什么吗?
她的医学教育里没有教过她怎么做,但是刚从尼泊尔旅行回来的妹妹给了她启示。在医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加德满都,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种特殊的方法帮助临死之人:第一种方法叫做“自他交换”,就是你试着深呼吸,并想象自己把对方的病痛与不幸都吸到自己身上,然后呼出自己的幸福与健康给病人;还有一种是听对方讲故事。于是她回到病房,开始尝试。
故事到了这里,我们似乎都可以预见的是,那个病人最终还是会死去,可是有没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呢?有,他得到了死前的慰藉。
2
这个话剧里垂死的病人,得了一种医学尚无法解释的绝症,一直发烧,但是找不到病因。我想试着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让我们站到男主人公这边来:当他面临突如其来的人生莫大的苦难时,他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他为何没有选择自杀,甚至没有意志消沉、堕入悲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由此,反观对人生最重要的基础教育里,有没有一些东西在教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种种困境?
当我在国内教完三年的高中后,我意识到我们的教育里最大的缺失是对人生本身的关注或者说对生命的关怀。不管物理化学不好,还是历史地理不好,它们大约都不会让你在今后的生活上直接栽倒。但绝对有人活了一辈子,回头反思自己一生的意义何在,才发现乏善可陈;也有人陷入罕有的绝境而未能绝处逢生;还有人并未检视自己已得的快乐,不知足也未能常乐;更多人在别人未知的角落不懂如何疗伤……我们的教育里没有任何一门课教我们如何平安度过此生。
我的学生就曾经问过我如下的问题:
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这么无聊,为什么父母们可以这样过一辈子?
我喜欢的人好像不喜欢我,怎么办?我失恋了怎么办?
人的一生最终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和别人无话可说?
……
我想指出的是,生活不仅仅止于此,人生无常、生命多艰。即使一生平安,生命的质量仍然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力。我们有教会他们反思自我的生活吗?他们能在教育里找到生命苦痛时的安慰吗?或者退一步,哪怕仅仅是获得安慰的线索。
3
写这篇文章的这个早上,我正好和我的新加坡学生一起上了一堂课。老师先给大家放了一个视频,记录的是新加坡的一些年轻人在闹市区现场问路人:什么让你感到幸福?放完视频,老师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写下最令自己感到幸福的六件事。同时要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自己认为的这些幸福作为追寻目标吗?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这群十四岁的中学生都以什么为幸福:家庭、朋友、食物、手机、睡觉、钱、音乐、没有作业、玩游戏、篮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想见那个要讨论的问题的意义所在,很多令我们感到幸福的东西,并不能无止境去获得。纵欲与追求幸福也只在一线之间。
这堂课的第二个部分是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老师给出几篇学生写的自身经历。其中一篇是写自己去一个落后的国家做志愿者,教那边的孩子英文,他发现那些贫穷的孩子对生命充满了热忱,他们过得很快乐,因为他们感激珍惜一切自己所得的。同时志愿者也觉得自己获得了幸福,因为凭自己的能力给那些孩子带去了欢乐,令他想到能给予他人快乐也是一种幸福。
学生在看完这几篇同龄人写的文章后,会有一个讨论环节,这个环节甚至可以进行组与组之间的交流。讨论的问题是:一、是什么让作者意识到生命中真正的幸福?二、他们怎么去创造这样的幸福?
讨论完后老师做了一个总结,给出自己的建议:
最后每个人需要独立思考并完成作业:
这堂关于幸福的课就这样结束了,我大概也不太相信这么短短的几十分钟,学生领会了人生幸福的真谛。但并不代表这堂课是无意义的。它会是一个人思考幸福的源头,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能经常停下来想想,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这样他们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离生命的本质更近,离迷失越远。
4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CCE,全称是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Education,可以翻译为:人格和公民教育。但事实上涵盖的内容非常之广,特别是它涉及了许多人生问题,让我来列出几个话题
这个课程还涵盖了安全教育、性教育、法律教育等等。但是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填补了一项空白:人生教育。
5
我有个新加坡教中文的同事,年届六旬,退休回来继续做老师多年。她性格开朗,办公室里常听到她婉转回荡的笑声,她经常自嘲:我讲话就是这么大声,真对不起。她对那些我们眼里不听管教的“差生”特别有一套,她自己也乐在其中。我们总觉得她过得特别自在。去年,我们几位同事说好年底假期一起去平遥古城,她是头一个响应的。但是临近期末的一天,她邀请我们一起下了趟馆子,狮城有名的粤菜馆。当饭饱茶酣之际,她道出请客的初衷:向我们表示歉意,她不能成行了。原因是她的儿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的儿子多年前与日本妻子离婚,得抑郁症,治疗的效果了了,终至于此。其他几位大概早有耳闻,而我听来却异常惊讶,我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在她身上竟有这样残酷的命运刻痕。
有一天我们一起看着学生参加活动,聊天之际,又提及此事,我说其实你知道吗,听了你的事,我不是一种同情的感觉,而是敬佩。我知道未曾真正经历过人生重大苦难的人是无法体会那种哀伤的,也不懂当事人如何能走下去,其实当时每一步都在悬崖边上,一念之差即是深渊。我对她说:所以我常常想,我们能教给学生的东西太少了,少到有一天他们遇到在我们看来的小挫折时,即对命运缴械投降,更别提真正的苦难。她笑了笑,似乎觉得他儿子亦然。可她对我说:我还是觉得有意义的,我有时会把自己的事换一个主人公,当作故事说给学生听,当时他们可能只是听一个悲伤的故事,可是真的有学生若干年后回来找我,和我讲她遇到的困境、她如何走出困境,而原因是她想起了我的故事。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6
提“教育的慰藉”这个概念,可能让教育承担了太过沉重的责任。可是,现今大学生自杀频现,甚至中学生自杀亦时有耳闻,还出现马加爵案、复旦投毒案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是不是都可以推给“精神病”呢?这都是当事人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而不是教育出现了问题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得心理疾病之前呢?是他们没有找到化解心中那块冰的途径。
最后我想讲另一个学生的故事,我带的课外活动是棋社,棋社里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他是坐轮椅上学的,平时他并无异常,谈笑风生,还是棋社里的象棋高手,我一直暗暗佩服他的坚韧。有一天,棋社活动,突然一个学生跑来和我说,他闻到教室的一处有臭味。我起身去看,他指的地方正好是轮椅男孩下棋之处。那个报告的学生开始喊:老师这里很臭。而轮椅男孩紧张地说:哪有?哪有?我怎么没闻到。我已经明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就一阵心酸袭来。他在生命中曾经遭遇多少次这样的无地自容,谁教会他继续第二天若无其事地重新出发呢?
2014/02/22
欢迎关注天使支教相关公共微信平台,参与相关话题讨论。
|
- 上一篇:高校毕业生:空虚的漂泊者
- 下一篇:伤害你的,是你对事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