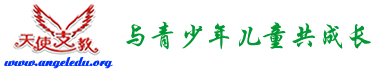卢安克眼中和手中的纪律 ——《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是什么给我力量》阅读札记
 王丽琴,江苏东台人。博士后,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曾任东台师范学校团委书记,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原江苏教育学院)教师。毕业于南京师大教育科学学院,获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学位,曾在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专著有《教学秩序初探》等,天使支教“教育创新研修班”导师。 卢安克眼中和手中的纪律 ——《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是什么给我力量》阅读札记
题记: 2015年暑假有幸给“天使支教”项目的志愿者授课,考虑到听众来源和需求很多元,我选择了“教学秩序”为主题。备课时频繁联想到卢安克的支教实践。他怎么看待纪律?他怎么建设和维护自己的课堂纪律?特意对两本电子书《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是什么给我力量》进行了扫读,找出其中与纪律问题相关的内容(蓝色楷体),红色加粗处则凸显我对他的观点的呼应。应该说,他是我以往田野考察中没有见识过的另一种管理风格的代表:温柔、忍让,同时又讲理、钻研。让我们一起从他的文字中寻找这种风格的纪律建设思路吧。
一、卢安克是不是太温柔? 以往的阅读以及视频浏览,相信大多数人都能认同这一点,那就是卢安克对学生极好,极耐心,孩子们在他身边可以表现得完全不同于跟其他老师在一起的放肆、放松。在《与孩子的天性合作》中,有这样一段对自己承担的英语教学的回顾,卢安克列举了学生的评价: 在已经离开这里的学生半年后,我让他们对我和其他老师的课做比较。他们说:听我的课能懂得比较多,学到的单词也多。还说:“你的课更好玩”,“其他老师只教书上的,太死板固定,你的课更活跃,能够发挥我们”、“我们很调皮只是因为知道你不是一个正式老师”,“我们太调皮,可还是希望你能管好我们”、“你太太太太太温柔,你应该凶一些,调皮的学生要很怕你才行。” 而在思考“纪律与性格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时,卢安克反思了自己有时也不够耐心,“我没有耐心,在学生突然跑出去时不知该怎么办,就到教室门口靠身体的力气来阻挡学生提前下课。可是这样做看起来很可笑,也使学生有机会捉弄我。”我们不难想象这个场景,如果换了我们常见的老师,不够耐心、不讲温柔的中国教师们,应该不会是这样的表现,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不够耐心(用身体阻挡学生)的行为,和大多数老师的行为相比,依然是足够温柔、太过软弱了吧。 学生对于卢安克的这种温柔和“软弱”是怎么看的呢?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他们喜欢卢安克,也时常拿这种不太普遍的管理方式开玩笑,以捉弄卢安克为乐趣, 我在宿舍了解到:他们非常愿意得到我的修改或批评,因为我的批评听起来很舒服、很温柔,也很好玩。 在看过一部日本侵略中国的电影后,有6个学生专门来捉弄我。我对他们说:“只因为我不凶,你们就用捣乱来惩罚我这种不凶的做法。你们用这样的做法要求我凶,凶到什么程度?像日本鬼子一样吗?我不是来对付你们,是来帮你们学习的,所以不愿意这么做。” 他们希望卢安克凶一点,对于卢安克不凶、不打架的理由,他们可能暂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相信,长大后他们会明白,也会因接触过卢安克这样的人,性格和人生因此有所不同。 说到温柔式的管理风格,我还联想到魏巍的散文中对自己一年级的美女老师蔡云芝先生的深情回忆: 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温柔的老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呀! 二、卢安克也关注权威、也使用惩罚 卢安克专门撰文《纪律与惩罚》《害怕才有威信吗》《意志与权威的关系》等,探讨跟纪律关系密切的权威、惩罚、威信等问题。其中关于权威,他的思考相当系统,且深入。 (一)什么是权威?为什么要有权威? 我初一学生的做法经常促使我思考:什么是权威?教育者们想出很多种方法,来让学生接受老师的权威,比如让学生在教室前站着、下课后把学生留在教室里等等。可是,为什么学生愿意就这么站在教室前、留在教室而不敢到处乱跑呢?他为什么愿意就这么接受惩罚呢?实际上,不是通过这种做法让学生接受了权威,而是通过权威让学生愿意接受惩罚,不管有权威和用惩罚方法的老师是不是同样一个人。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依稀能发掘,卢安克眼中的权威,其实先于惩罚,也就是说,权威不是惩罚的结果,而是惩罚能够开展的前提。那么,为什么孩子需要这种几乎是老师先天存在的权威呢? 他们调皮和给我带来难题的做法实际上只是在考验我的做法,看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他们希望我要成为的权威。其他班的许多学生叫我“老大”或者“爸爸”,他们需要我成为他们的依靠和权威。 原来,权威也是依靠!用“天使支教”项目引发的手册上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而言,权威,也是归属,是儿童特定阶段必须获得的,不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比如,意志能力的缺失、成年后的自我意识不够独立等。 如果在小孩年龄(幼)时自由,他们成为成年人时就不自由,无法去控制自己所做的事情(低级的范围来控制了意志)。如果在小孩时不自由(听话、服从和服务),他们到了成年时就有了足够的能控制自己和让自己自由做事情的力量。学生的意志能力是老师先要控制和培养的,可是他们以后要独立出现的自我意识,却是我们永远不能控制的。 卢安克对留守儿童这方面的缺失,有着极深的忧虑,因为他们身边,缺少了大人,缺少了权威。 在农村的未来,权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父母去城市打工,小孩从4岁就开始住在离家很远的学校,跟同学们自立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生活老师),他们基本上都是小孩跟小孩在一起,没有大人当权威。
(二)权威的建立有哪些阶段?如何得到? 作为华德福教育思想的传承者、实践者,卢安克深信该理论对儿童身心灵发展阶段的判断,其中关于权威的建立,他认为小学四年级和14岁是重要的关口。 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生再也不会随便相信一个老师。如果要继续保留权威,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权威,也就是通过给学生看。 还没到14岁的小孩,因为自我意识还没获得自由,所以意识不到别人的心理。……一个人的忧郁形态不可能抓住还没到14岁、急躁型同学的兴趣,也不可能相反。14岁之前,一个学生表演自己性格的角色才会有调整作用。 更难得的是,他在考察这些具体阶段的权威需要特征时,还兼顾到了不同性格类型孩子的差异。 到了14岁、有了个人独立的自我意识出现后,起作用的是与自己性格相反的。这时,急躁型的青少年才会发现忧郁型的小孩跟他自己的不同,使他思考起来。通过看到别人跟自己的不同,他会去意识到自己的特点和自己对别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 既然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都需要一定类型的权威,老师该怎样扮演这种权威角色,且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化呢?卢安克强调的是信任、共同工作,而反对威压、机械式的课程安排等不健康的权威手段。 这里所说的权威当然不是通过压力(威力)达到的,而是通过互相的信任、信赖和共同工作达到的。……为了让学生信任老师的权威,老师不能根据上级部门的安排去实践他的课程,而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良心去创造。为了能当学生的权威,老师还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自己的学生。只有老师允许学生的事情影响到老师的命运,学生的心才会接受并发生过程。 卢安克在很多主题下都谈到这种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学生的价值观,权威的建立也是如此。但,在较早的文字中,我们依然能发觉他对自己这个信念的追问和反思: 那么,真正的权威到底是怎样得到的呢?我初一学生的班主任在上课时会把脚放在桌子上看报纸,而让学生自学。学生为什么都很听他的话,不听我的?只能通过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学生而得到。不过,我还不能放弃自己在县城学校和北沟村的生活,还没有把我整个生活奉献给学生。 也就是说,卢安克看到周边的老师惯用的权威模式,是有自己看法的。他始终相信,只能通过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学生而得到真正的权威,但自己之所以暂时不能让学生很听话,原因可能是,当时的自己还没有做到把整个生活奉献给学生。
(三)惩罚的必要性和不当惩罚的后果 卢安克的文字里面也有一些惩罚的痕迹,比如“后果呈现”和“现身说法”: 有时,个别学生因为想给我添麻烦,专门来反对我的做法。我就尽可能给他订下实现更好做法的任务,让他的做法得到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结果,使他下次会考虑得更周全一点。我想把后果很自然地从学生的做法中发展出来。 有一天,我在一个初一班尝试让最调皮的学生狠批了一通全班同学做的跟他一样的事情。我当时想,学生很崇拜勇敢调皮的同学。而调皮的同学对大家说不要向他学习时,他就没了继续调皮的原因,同学也没有原因来佩服或支持他。 不过让他们说的过程中,这几个乐观型的学生说得很好玩的样子。虽然当时没得到什么结果,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我还是让另一个既害羞又调皮的学生这样做。这个同学的问题虽然最大,而且他安静了5分钟后才敢开始认真说话,可是全班都很重视他批评同学态度的话。 卢安克一边尝试着各种惩罚的办法,一边进行反思:这些惩罚是否有用?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我惩罚学生,有的学生当然会生气,而会生气的那些学生才会从惩罚中学习。所以,我不怪他们生气,反而对他们说:“你生气了吗?不要紧,你就生气吧。”我也不是因为反感才去惩罚,而是为了帮助他。 我想,惩罚是有必要的,可在惩罚学生时我注意了:惩罚不伤害学生的灵心、心理动力、生命力等,因为我想避免他们从自己改变自己所需的力量萎缩。惩罚要破坏的是,学生以为不参与调皮活动同学就看不起他们的想象,因为调皮学生就被这种想象控制着。然后我不说他的不好、他的缺陷,只跟他谈将来解决的方式。 卢安克的惩罚方式,当然也是相对温柔的,并且很重视惩罚后的交流,不说学生的不好和缺陷,而只谈将来解决的方式,这无疑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他对惩罚目标的认识,也与很多老师不一样,不是为了出老师内心的气,也不是为了对不良行为的纠正简单。他希望自己的惩罚能改变调皮学生头脑中的错误想象,而只有摆脱了这种错误想象,孩子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喜欢这样的惩罚目标,也深知,极不容易。 他也明确反对打骂孩子,尽管身边的成年人和孩子,似乎都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惩罚。 打小孩的年轻人和家长对我说:“我们这个方法最见效。你看,我只要打他一次,不管要做的事多难,他就马上做到。”这是为了效率而思考,但得到这种效率之后呢?心理损害呢? 这都使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甚至已经没有感情。对他们还能留下印象的只是更凶、更可怕的人和事。……很多老师也利用不自然的威信方法来代替学生对他们的承认。不过,这种惩罚只会使学生越来越不老实,只去考虑如何避免麻烦,根本不敢用自己的心里想法参与课堂。压力、惩罚和害怕的方法不只压制了学生的调皮活动,因为影响他们生命力的发展,同时也压制了学生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和健康。 这些后果,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着,延展着!老师们,是不是要认真考虑一下卢安克的建议,慎用惩罚,尤其是伤害孩子生命力、创造性和身心健康的那种惩罚!
三、卢安克更多在研究,而不是简单地被纪律而烦恼、而生气 之所以敢于做这样的判断,是在大量的行文中,读到卢安克的描述与分析都是很冷静、很耐心的。他一直也苦恼于外界只关注他的传奇故事,而不关注他的研究过程与结论。我想,“研究者”,大概是他最在乎的身份。在纪律问题上,他也确实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分析,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如以下这个案例: 我一个初一班的班主任把全班三个最调皮、同样急躁和乐观型的学生分开坐在教室之间距离最远的位置。这使得全班在他们之间受到了影响,而且因为这三人互相距离很远,所以他们要反应得特别厉害、声音特别大才能沟通。其实,如果这三个性格相同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就会因为性格单调而互相厌烦起来。 我联想到跟“天使支教”志愿者们分享过的薛瑞萍老师如何看待座位安排,“后排稳则班级稳”,班级最优秀的孩子,往往集中在后排。这个观点与做法,显然跟大多数一线教师不一样。同样,不少老师认为,调皮的孩子要分开,免得相互影响,但卢安克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与其这样相距遥远,使得他们反应更厉害、声音更大,不如让他们坐在一起,时间一长,“性格单调而互相厌烦”这个因素,反而使得他们对班级秩序的破坏性会降低! 卢安克的研究者心态还表现在,会很客观地评价某个办法的有效性。在一个地方无效的办法,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班级却有了很好的效果。当然,有效时间也不长: 我在县城无效的做法,也就是让一个学生说他和全班同学的态度,在农村初一年级却有了很好的效果。这些真实的话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只是有效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个做法需要学生有良心。 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对教师处理纪律和管理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种管理方法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必须常换常新,因地制宜。而透过这些观察与分析的表面,笔者更欣赏的是卢安克已经有很深入的分类、分层思维,比如在《“纪律与性格有什么关系?”》一文中,他在学生性格上的分类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如果不只为纪律着想,而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我们就会这样考虑:教育不同脾气的孩子需要不同的态度:暴躁型(急躁型)的孩子需要一个他能崇拜的、能做到学生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老师,这就是不发火,冷淡。……老师对暴躁型的小孩需要冷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如果忧郁型(冷静型)的小孩看到比自己更惨的事情,就会脱离对自己感情的过分重视。如果老师让这一类型的学生看到别人面对的困难,忧郁学生自私的感情就会变成对别人的同情和关心。所以老师需要给这样的小孩一种特别会引起他们兴趣和做出判断的事情。 乐观型的孩子特别需要能看见的和探究的事情,对于这一类型的孩子,老师需要是特别认真、他们能爱的一个人。学习内容需要满足根据性格的兴趣、习惯、愿望或特点,不过也需要发挥孩子的坚持能力。 稳定型的孩子需要一个表面上和他自己一样、可是心里对他非常发挥兴趣的老师。 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发现了暴躁型、忧郁型、乐观型、稳定型等性格类型的孩子,需要不同类型的教师性格加以引导。虽然这些类型划分,从已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看,也并不新鲜,更接近于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的气质类型经典划分,但,当教师把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学生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看时,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在涌现。卢安克接下去分析: 前边说的是学生需要的老师。不过,学生的互相作用和老师对学生的作用不一样:老师需要发挥学生缺少的性格,可是学生需要互相“擦拭”掉自己太片面的性格。 这里又多出一个维度,即,生生之间的性格匹配。如果说师生之间的性格匹配,卢安克认为应该是尽可能互补,即发挥学生缺少的性格特征,那么学生之间的相互“擦拭”,我理解大概是允许相同性格类型的,一起活动、一起碰撞,而不是很多老师习惯的,让安静的学生和活泼调皮的相互搭配。这个观点之后,卢安克就主动呈现了前面的那个案例,用以佐证这种生生相似性格互相擦拭的尝试,事实证明,效果不错。 在上课过程中,我叫那三个同样影响课程的学生一起到没有其他同学的地方两节课,让他们自己闹着玩、彼此厌烦。我还说,他们爱提前乱跑,应该喜欢这样。结果,他们三个人很安静,因为没有了同学做缓冲器,所以觉得没出力的机会,太单调,并且总是尝试回到班里。从此以后,就没有学生再提前乱跑下课。 其实,只要老师以这种研究的心态来面对纪律问题,一般就不会再徒然地陷于跟学生生气的状态,卢安克也反复提醒过,不要轻易发火,对一个12、3岁的孩子乱发火,他们长大后,到四、五十岁了,还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如肚子疼,等等。
四、卢安克的以身作则和不断认识自我 作为老师,在进行纪律建设时,必然绕不开“以身作则”这个基本原则,卢安克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在《“哪里有学生考老师的情况?”》一文中,他反复强调教师的示范性之重要。 为了能通得过学生的“考验”,我非常注意帮他们完成和做到所有我要求的事。 为避免“应考”不及格,我非常地注意不随便要求学生做我不能保证他们做到的事。 他长期和留守儿童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和归属感,以下这段文字,细读者一定会非常感动,可以触摸到卢安克是如何用心灵来感受孩子的心灵,又是如何用行动来回应孩子的需求。 学生躲藏起来是因为他们希望被寻找、被找到;他们犯错误是因为希望得到我的关心(改正);他们逃跑是因为想得到我的保护(安全);他们打架是因为很想得到同情的感情;他们吵闹是因为希望被注意(被惩罚),有时也因为闹,所以心理紧张得更加闹;他们敲诈我是因为希望我来证明他不会被勒索;他们欺负我是因为希望体验到后果;他们想自杀是因为希望被救;他们生病是因为需要被治病;他们调皮是因为需要被爱。 我想,如果我们每位老师能够这样的把自己的全身心融化到孩子的体验、孩子的需要之中,“以身作则”这个相对传统的术语,就可以升级换代了。到达这个境界的老师,不会感到自己被诸多的为师原则所捆绑,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孩子身边的榜样、权威,以及依靠。 卢安克还在行文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性格特征,从自身成长的历程寻找教育的元素,实现作为教育者的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 我想起自己做小学生时,是班里最忧郁型的学生,被安排坐在最急躁、最调皮的学生旁边。他所有多余的力量我都接受,都放在心里,并没有反抗的能力。他因为感觉不到我在反抗就认为需要更加加强才行。有这么好欺负的同学,就很容易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厉害。 在搞活动时我又发现:我这个人虽然能发现问题,可是不适合教师职业。别的老师的自我很自然就能做到的事,我却感到很困难。根据我不敢表现自我的性格,我经常好像不在现场一样,给学生留下一种空白感。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他说过这个现象的原因。他说,不在场的是我的自我意识。我不敢让我的个性和自我表现自己。结果,我就当不了学生的权威。学生也觉得好像我不在,也不能尊重我,就乱了起来。学生就需要我的自我意识来控制和培养他们的意志,他们依靠老师的自我意识。……学生需要那种总是主动的老师。我这种被动、能观察的特点,其实更适合做研究工作。 卢安克到底适不适合做老师?尤其是不是适合做中国乡村留守儿童的老师?在2000年他结束一段初中教学生涯时,《艺术的本质》一文中描述了他的课程给学生留下的影响: 现在已经初二的我的学生变化很大,每个人的不同特点现在都很明显,他们的变化感动了我。班主任说,我的课留下的影响是,现在学生的纪律比其他班难管,主要是60个学生中有10个喜欢乱跑或抽烟。可他也说,我的课留下来的影响是,学生的思维、想象力和素质变得特别好。 纪律比其他班难管,但学生的思维、想象力和素质变得特别好!我想,这个判断很能说明问题,而我们要判断卢安克是否适合当老师,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希望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如果只是纪律好管,那卢安克的管理风格,很多时候会遭遇失败。 卢安克在纪律方面也取得过好的成绩,在《 “你能不能帮我当班主任?”》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代理班主任的一段经历,通过与原班主任的合作,他们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我慢慢发现,我们的班主任韦阳东是个做事完美的人。很多跟别人不能谈的事,我们却很喜欢谈。他说见到我就对教育有信心,而我说见到他就很放心。班里学生也感觉到了我们的合作和互相尊重,而他们发现和感受到这一点,使全班得到了一种力量、放心、平安和信心。 结果,我们的学生也同样合作得特别好,能集体安排全班的事,比如野炊等,不需要老师来安排。我们让学生自己安排野炊、晚会、座谈会等活动。老师只把他们分成四个组,规定时间,在活动中我们只当客人。 我重视学习方法越来越少,重视和班主任的合作越来越多。我们班成绩虽然比较差,可全班不仅在纪律方面每个星期获得第一,也在体操比赛中合作得最好,获得了全校第一。 这段描述告诉我们,卢安克的管理风格如果遇到相对开明、且有能力的班主任配合,效果可以很不错。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卢安克的心胸始终是开放的,在完成了纪录片之后,他看到邻屯的志愿者也在做类似的活动,这篇相对散漫的《别人可以做得更好》,描述了自己对别人做法的观察与点评。 我看到别人开展的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内容)的活动,而因为简单,所以非常清楚。学生从这种简单得到的就是我复杂的活动给不了的安宁。从这一点,我学到了很多。 下次为了让学生有足够的安宁去创造,我也要选择最简单的方式,特别是跟低年级的学生。……邻居村的一个退休的志愿老师也就是这样做的:在教了那边3年级一年之后,她还开了一个扫盲成人班,使成人学生还想做书等等。 卢安克的这种生命状态,真的让我肃然起敬。他不断地反省自我、观察周围,然后接着反省自我。虽然他关于纪律的看法和做法,谈不上完美,但,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自我在为教育而努力,我看到了教育的美好和希望所在。
卢安克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的纪律观、管理行为也许不能被我们直接沿用,但,他的存在,对“教学秩序”这个课题而言,就是一个难得的财富,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