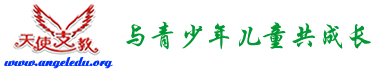如今的大学生去支教,可以说他们根本从未思考过教育的内涵,他们以为拿着课本,将中原的那一套教育体系,那一套自己接受过的并已经深陷其中的被毒害良久的教育体系移植到藏族身上便完成了支教的使命,实在是太愚蠢。真愚蠢! 请问如果这样做,最好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对,就是把我们经历的现有的考试制度,培训班制度,题海制度等等完全移植到藏族身上,然后让他们有能力参与到我们的“考大学”竞争比赛中。否则他们依然是“教育”的末端,按我们说的,“无法找到好工作”、“无法幸福”。 首先,即是这样做是对的,你是否能花若干年办成这样的事?即将汉族的教育制度完完整整的移植过去,让他们跟我们一样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竞赛? 其次,即使办成了,我们的结果呢?藏族的孩子沦亡成新一批的教育受害者?跟我们一样?藏地变成了跟中国几百个城市一样的发展模式?请问,我们现在羡慕西藏不正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么?然而且不说能否跟我们这样的孩子进行竞争?即使成功考上一所大学,之后呢?重复我们的教育悲剧? 再次,我们有没有问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工作?是职业和收入?那不是目的,那是手段,工作、职业、收入的目的则是是生活幸福。快乐。而我们看看,我们幸福么?快乐么?相反,我们往往却觉得藏族孩子的微笑很真实,他们很幸福!那么,我们的整个系统是不是就是失败的呢! 我们觉得藏族落后,然而我实在的告诉你,我们的目的是幸福,并非物质的充裕,一个藏族孩子没有最新款的手机,没有来自欧洲知名品牌的化妆品,但他会比拥有这些的你更快乐!我实在的告诉你,商品、广告已经把你裹挟在其中,你已经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藏族社会已经有循环近千年的秩序在其中。 他的宗教已经充当了法律,而这种“法律”根治在人们的心中,不是在犯罪之后的惩治,而是在有犯罪念头的时候告诉人民敬畏,那么犯罪便不会发生。 当供养寺院的钱被用到对于基层的建设中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民众的物资收入进一步提高,便又可以继续供养,形成一种循环的机制。如果说一个地区越贫穷,政府花在该地的维稳经费就越高的话,那么这个准则很难在藏族社会中运用,因为藏族民众即是贫困,也会一心向佛,这已经充当了社会的稳固支柱。 我们一无所知,且盲目自大,我们以为落后的社会就应该被我们同化,就应该被我们所取代。那么,在19世纪鸦片战争,英国是代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难道它有资格取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同意那个,然而现在,我们却用这种思维来潜移默化藏地的秩序,何其可恶。 正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说,任何组织,机构都是在抑制每个个体的思考能力,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组织。因为组织的规则,或者说理念必然会迫使这个组织的成员达成某个可见的目标,任何支教的组织都是如此,是想达成某种目标的,刻意的去“改变”某种现状的,或者相反的就是,一个支教组织连达成某种目标都没有,这则更为无意义。 那么,我们支教的意义是什么?你首先可以排除了考试,你接着可以排除了如今的教育,你的结论可以是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为自己负责等等等等的,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支教”是与教育无关的一种行为。而我接着问你,关于未来,关于为自己负责,这些东西是通过所谓“支教者”来教给他们的么?或者说,支教者们,自己有没有真正想清楚这些问题!或者说,他们所谓的理想,是否是适宜的? 往往一些无意义的思想,实际上,打碎了一种原有的思维,进而是当地秩序的混乱,科巴原有的宗教维持一种循环和平的机制,而如今你告诉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去外地打工,去西宁,去北上广,去东莞,然后呢?跟我们一样?然后呢?老人留在村子里孤单的活着,守着无人信仰的信仰。 我现在再反过来问你,什么,是,教育的,意义?你能否回答,我告诉你,教育,就是维持着一种地区特定秩序的运转。 如美国,最早的教育是让公民懂得民主的意义,维持美国的民主秩序的运转; 如西藏,最早的教育是在寺院中,让孩子们懂得敬畏,这种敬畏充当着法律,维持着社会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区域体内部民众供养僧人——僧侣协助地方权势护佑政权并以宗教伦理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的稳定保证区域内家族式经济的传承——经济的增长得以继续供养僧侣”。 这些都是教育,而支教者们做的,是把自己奉行的一套价值体系,自己的一套自己都不知道的价值观强加到藏地上,这最终的结果是摧毁一种平稳的社会,整个社会变得万劫不复。这就是我们,无知的我们,做的事情。 我最后的问题是,这群支教者,这群教育的残次品,这群被外界价值冲击的,庸庸碌碌的,为工作而奔波,借支教来自娱自乐的人,究竟是一群什么玩意儿,能改变什么?——这其实不过是文革的遗毒,是毛腊肉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种垃圾思想的残种罢了。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dshell_js").src = "http://bdimg.share.baidu.com/static/js/shell_v2.js?cdnversion=" + new Date().getHours();
- 上一篇:有一种爱,那是在害 别再给偏远山区孩子糖果
- 下一篇:假期大学生短期支教引争议